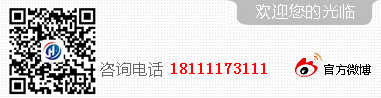兩起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政復議案
【案例一】經營藥品零售的G公司一直與Y公司有采購業務往來,該公司2014年向Y公司采購藥品,取得Y公司開具的18份增值稅專用發票。2017年,Y公司所在地甲稅務局稽查部門認定這18份發票為虛開發票,并向G公司所在地稅務稽查部門出具《已證實虛開通知單》。不久,G公司被所在地乙稅務局稽查部門立案檢查。
乙稅務局稽查部門調查取得涉案18份發票的銀行轉賬憑證和G公司管理人員的詢問筆錄。有關陳述只表示公司存在真實交易,貨物由Y公司通過汽車運輸送達G公司,不能提供購銷合同和相關貨運證明。稽查部門認為,G公司未能提供與Y公司相關業務的購銷合同,雖有轉款憑證及Y公司通過汽車運輸將貨物送達G公司的言詞證據,但無貨運單等其他客觀證據予以佐證,無法確認G公司與Y公司的有關交易系真實發生,不能反映有關交易的貨物流、資金流、票流等是否一致,不足以證明其取得Y公司18份發票存在真實交易。最終作出稅務處理決定:G公司從Y公司取得的18份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所涉進項稅額不得從銷項稅額中抵扣,補繳相應的增值稅及其附加,加收稅款滯納金。
G公司提起行政復議,乙稅務局經復議,以部分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撤銷有關稅務處理決定。
【案例二】S公司于2017年向B公司采購一批設備,取得B公司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一張并于同年認證抵扣。2019年,B公司所在地J稅務局稽查部門認定該發票為虛開,并向S公司所在地N稅務局稽查部門出具《已證實虛開通知單》。同年,S公司被N稅務局稽查部門立案檢查。
檢查中,檢查人員取得涉案購銷合同、蓋B公司財務專用章的現金收據和送貨單、對S公司負責人與財務負責人的詢問筆錄。其中,現金收據上的貨物交易信息與送貨單的單價、數量、金額信息一致,也與購銷合同的有關信息一致,筆錄也沒有矛盾之處,被詢問人都表示與B公司的交易真實。
N稅務局稽查局認為,S公司提供的購銷合同、收據等無法證明其與B公司存在真實業務,從B公司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違法事實已被行政機關確認,根據有關規定對S公司作出稅務處理決定:案涉發票系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所涉進項稅額不得從銷項稅額中抵扣,應補繳相應的增值稅及其附加,同時補繳稅款滯納金。
S公司提起行政復議,N稅務局經復議,以部分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撤銷有關稅務處理決定。
爭議焦點:是否善意取得虛開專用發票
這兩個案件中,稽查局均已取得開票方所在地稅務機關開具的《已證實虛開通知單》,要求受票方將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作進項稅轉出并補繳相應增值稅稅款,不存在爭議。爭議焦點主要是:兩個案件中的購貨方均認為其構成善意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依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納稅人善意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已抵扣稅款加收滯納金問題的批復》(國稅函〔2007〕1240號)規定,應當不予加收滯納金。而稽查局認為,檢查取得的證據無法證明購貨方的有關交易真實發生,無法認定其構成善意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
什么是善意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納稅人善意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處理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8〕187號,以下簡稱“187號文件”)規定,在購貨方(受票方)不知道取得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以下簡稱專用發票)是銷售方虛開的情況下,購貨方與銷售方存在真實的交易,銷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的專用發票,專用發票注明的銷售方名稱、印章、貨物數量、金額及稅額等全部內容與實際相符,且沒有證據表明購貨方知道銷售方提供的專用發票是以非法手段獲得的,對購貨方不以偷稅或者騙取出口退稅論處。但應按有關規定不予抵扣進項稅款或者不予出口退稅;購貨方已經抵扣的進項稅款或者取得的出口退稅,應依法追繳。
由此可見,“購貨方與銷售方存在真實的交易”等三個界定,是善意取得虛開專用發票的三個構成要件。其中第二個構成要件較為直觀,最難判斷也至關重要的是第一個構成要件(購貨方與銷售方存在真實的交易)。
具體到本文討論案例,查處案件的關鍵是,能否證明開票方與受票方存在真實的交易。然而,由于有關交易已歷經數年,稅務機關對有關資金流、貨物流等調查取證存在困難。此外,由誰對有關真實交易承擔舉證責任,以及什么證據資料足以證明存在真實交易都存在爭議。
誰對善意取得(存在真實交易)負有舉證責任?
有觀點認為,依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行政機關對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應當負舉證責任。即理論上,稅務機關認定購貨方非善意取得虛開專用發票,應當對其認定負有一定的舉證責任。但舉證一個消極事實是強人所難,行政行為的舉證責任是否必須參照行政訴訟的舉證責任也值得商榷。
筆者認為,可以參考行政處罰法中關于主觀無過錯證明責任的規則,是否構成善意取得虛開專用發票,由購貨方負責舉證證明,稅務機關有權決定是否予以采信。
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的新修訂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三條第二款,首次明確行政處罰適用過錯推定原則,規定“當事人有證據足以證明沒有主觀過錯的,不予行政處罰;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該條款雖適用于行政處罰,本文討論的是稅務行政處理的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但結合本文案例,根據187號文件規定,如購貨方被稅務機關認定為不是善意取得虛開專用發票,極大可能以偷稅或騙取出口退稅論處,即使不以偷稅或騙取出口退稅論處,購貨方也將承擔加收滯納金的不利結果,這與行政處罰中行政相對人承擔懲戒后果在行政法律效果上是一致的。稅務機關在該事項認定中,可參考適用行政處罰法中關于主觀無過錯證明責任的規則。原則上,稅務機關僅需要證明當事人取得虛開專用發票,是否構成善意取得,由購貨方承擔舉證責任。對于購貨方在稅務機關限期內提交的證據,稅務機關有權予以審查,根據審查情況決定是否采信。
不過,并非所有情況都適用主觀無過錯證明責任規則,根據證據規則運用要求,有些情況下舉證責任將倒置回稅務機關。
采用優勢證明標準還是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
稅務行政行為是采取優勢證明標準還是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由于沒有明確規定,實務操作中一直存有爭議。
案例一中,稅務機關是否應以排除合理懷疑為證明標準,有必要進一步前往銷貨方所在地對是否存在真實交易進行取證,進一步對有關資金流進行調查取證?或是應以明顯優勢證明為標準,僅在取得《已證實虛開通知單》的情況下,以購貨方沒有購銷合同、沒有物流憑證等事實情況為佐證,即可認定不存在真實交易?
案例二中,如以明顯優勢證明為標準,在購貨方無法提供轉賬憑證,但能提供相互印證的購銷合同等證據情況下,即使數十萬元貨款以現金形式支付缺乏交易合理性,是否足以認定構成存在真實交易?若以排除合理懷疑為證明標準,是否應進一步對銷貨方是否存在真實貨物交易調查取證,形成證明無貨交易虛開的完整證據鏈?
關于證據規則運用,筆者認為一般情況下應采用明顯優勢證明標準,對涉及虛開金額巨大或稅款滯納金金額巨大的案件,應采用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
民事訴訟中一般采用優勢證明標準,即當證明某一事實存在或不存在的證據的分量與證明力,比反對的證據更具有說服力,或者比反對的證據可靠性更高,采信具有優勢一方當事人列舉的證據認定案件事實。而刑事訴訟中采用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即無罪推定原則。
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行政訴訟雙方當事人的行政訴訟權利與義務關系不完全對等,介于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兩者之間。因此,有學者認為,在行政訴訟中,一般應當采用介于兩者之間的證明標準,應當適用明顯優勢證明標準。在行政行為中,可借鑒以上證據證明標準,對涉及行政相對人人身自由、重大個人利益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應采用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對一般行政行為采用明顯優勢證明標準。
就稅務行政行為而言,從追求稅收行政效果與效率相協調的角度出發,對于涉及重大財產利益,如涉及金額巨大的稅務處理或稅務行政處罰案件,或涉及人身自由,如涉嫌刑事犯罪將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案件,應當采用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除此之外,為提高征管效率、降低稅收成本,一般的稅務處理或稅務行政處罰,可采用明顯優勢證明標準。
回到本文討論案例,對于已認定取得虛開專用發票所涉稅款金額不大的案件,可采用明顯優勢證明標準,即把購貨方提供的證明其存在真實交易的證據,與稅務機關初步懷疑虛構交易的證據相比較,證明存在真實交易的證據更具明顯說服力的,可認定購貨方存在真實交易。對于已認定取得虛開專用發票所涉稅、滯納金金額巨大,或涉嫌犯罪案件,則應以《已證實虛開通知單》為線索,向開具《已證實虛開通知單》的稅務機關調取相關證據材料,或針對銷貨方直接開展調查取證工作,采用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完善無貨交易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證據鏈。
【晶晶亮讀后感】
我贊成作者的觀點。
對于取得虛開發票,如果是惡意取得,應該由稅務機關舉證;如果是善意取得,應該由納稅人舉證。還有一種應該是非善非惡,雖然理論上并不存在,但實務中,確實存在這種狀態,是因為雙方都沒有充足的證據,證明取得虛開發票是善意還是惡意,因舉證上的僵局形成的一種類似薛定諤的貓的狀態。
—END—